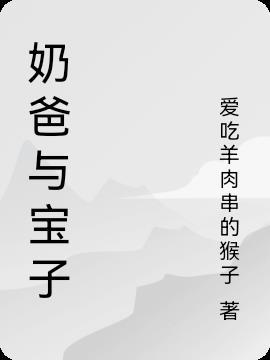《奶爸与奶妈》第414章 告别
上的外套,目光落在不远处那个佝偻的身影上——父亲陈守业正蹲在行李箱旁,反复检查着捆扎的绳子。那只旧行李箱跟着陈阳从高中用到大学,边角已经磕得发白,此刻被父亲塞得满满当当,外面还裹了层防雨的塑料布。 “爸,不用缠了,火车上不会淋雨的。”陈阳走过去想扶他起身,却被父亲一把挥开。 “你懂啥,这箱子拉链松了,万一颠开,衣服撒一路多麻烦。”父亲的声音裹着风,有些发颤。他的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关节处泛着暗红,那是常年在砖窑厂搬砖留下的印记。陈阳看着他费劲地系着死结,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这次,他要去国外读博,一去就是五年。 陈阳从小就知道,自己和父亲不是一类人。父亲没读过几年书,一辈子和泥土、砖块打交道,话少,脾气还倔。而陈阳爱读书,从小学到高中,奖...
《奶爸与奶妈》章节列表
- 第1章 爸爸帮忙写作业
- 第二章 未命名草饭桌上的接力
- 第3章 父子间的滑行冒险
- 第4章 会走的箱
- 第5章 上阵父子兵
- 第6章 好像呀
- 第7章 头顶上的默契
- 第八章 时光里父子和弦
- 第9章 靶心之外的外承
- 第十章 镜子里的小秘密
- 第11章 父子间的较量与传承
- 第12章 时光里的父子和解
- 第十三章 豪庭杂技
- 第14章 哄睡觉
- 第15章 父子间的那座桥
- 第16章 山人自有妙计
- 第17章 父与子
- 第18章 寻子记
- 第19章 甘为孺子马〞
- 第20章 复仇计划
- 第21章 儿子的挑衅行动
- 第22章 过分的指责
- 第23章 四个儿子四张票
- 第24章 精彩的瞬间
- 第25章 小鱼的信
- 第26章 父父与子子
- 第27章 顺利解决
- 第28章 梦游
- 第29章 遛狗奇遇
- 第30章 一年之后
- 第31章 槐树的年轮
- 第32章 入迷的游戏
- 第33章 死性不改
- 第34章 生日惊喜
- 第35章 这下了
- 第36章 输不起
- 第37章 落日画
- 带三十八章巷口里的父与子
- 第三十九章 铜喇叭里的泡泡宇宙
- 第40章 奇怪的胡子
- 第41章 罪魁祸首
- 第42章 太好玩了再来一次
- 第43章 踢球
- 第44章 梧桐树下的家
- 第45章 梦与现实
- 第46章 旧日单车与斩梦想
- 第46章 岁月里的温情长卷
- 第48章 不值得帮
- 第49章 人靠衣装马靠鞍
- 第50章 按顺序来
- 第51章 救火
- 第52章 艺术作品
- 第53章 时光里的父子印记
- 第54章 时光里的纸飞机
- 第55章 梧桐树下的秘密
- 第56章 训马
- 第五十七章 惊喜的一天
- 第58章 纸飞机与星空
- 第19章 风筝线的两端
- 第60章 输的精光
- 第61章 差一点儿
- 第62章 父亲的签名
- 第63章 放生的遭遇
- 第六十四章 时光里的父子情
- 第65章 大书迷
- 第66章 医生的嘱咐
- 第67章 神投手
- 第68章 没骗你真调着一条大鱼
- 第69章 藏在床底下的秘密
- 第70章 结果很好
- 第71章 滑冰
- 第72章 一碗阳春面
- 第73章 病房里的月光
- 第74章
- 第75章
- 第76章
- 第77章
- 第78章
- 第79章
- 第80章 沉默的河
- 第81章
- 第82章
- 第八十三率
- 第84章 装父亲
- 第85章
- 第86章
- 第87章
- 第88章
- 第89章
- 第90章 意外惊喜
- 第91章
- 第92章
- 第93章
- 第94章
- 第95章
- 第96章
- 第97章 丛林冒险记
- 第98章
- 第99章
- 第100章 山路上的回声
热门小说标签
和最强在一起之后我变成了娇小姐的七零年代穿书免费阅读苍穹之上浮岛之间谜底是什么物品穹顶之下完整版解说七零年代拖拉机什么才算十方功德月中僧男主破戒第几章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剑修今天不修剑夜兔娇小姐的七零年代穿书真少爷在豪门捡垃圾娇小姐的七零年代穿书转转风精灵月中僧女主和男二有过关系吗夜兔是什么动漫十方调唱佛功德赞和最强在一起之后我变人了免费阅读十方修行成正果入门赘婿林阳夜兔的弱点我们剑修不讲武德txt战锤以涅槃之名笔趣阁最新章节真少爷给重生豪门大佬冲喜和最强成为同期之后免费阅读莫教踏碎琼瑶什么意思70年代拖拉机图片大全掠爱成婚江烬个人简历我们剑修不讲武德全文免费阅读阴婚鬼事全文免费阅读战锤以涅槃之名无错版网站地图纵横修真小农民 魔帝,丹尊她又作死了 我在古代办妇联/欠系统六个亿,我靠种田爆富了 黑粉和爱豆结婚了/继承者驾到:校草,闹够没! 炮灰女配来自邪恶阵营 陆爷家的小可爱超甜 重启修仙纪元 [综]虽然我是汤姆苏,但我还是想谈场普通恋爱 柯南之多个侦探 快穿:万人嫌被变态坏狗们觊觎 (综影视同人)[综]炮灰终结者 治愈快穿:黑化男神,来抱抱 无敌小农民 死对头,我们配一脸[GL] 我是被抱错的那个? 龙珠:贝洛尔塔 双向奔赴?腿断了我们还能爬 太古玄幻神王 顶级A的Enigma又骄又野 醋缸打翻,被病娇大佬宠成小废物/病态占有:偏执陆总嗜她如命
本月排行榜
- 暖宠学神:漫漫追妻路舒蕊
- 魔君系统苍在笙
- 娱乐圈撩汉日常月亮和猫
- 李准王嫣然狗大户
- 小欢喜:超级学霸鸡尼太美
- 我真的不是邪神走狗起点御井烹香
- 海的儿子雅香
- 穿末世肉文之女配風過水無痕
- 满级大佬靠玄学征服全球青衣埋骨
- 做你的靠山桃禾枝赵十余
- 无耻宗主系统彩衣娱圣
- 无敌于鬼灭之刃鬼叔
- 默狱(高h文)默狱
- 重生八零之盛世枭宠古欣
- 我的知识能卖钱我渴望力量
本周收藏榜
- 洪荒古纪俺是张飞
- 重生之人渣反派自救系统墨香铜臭
- 我在沙漠里开加油站二马示羊
- 女帝们看到我的前世,全体泪崩!哥斯拉上天
- 学神您搞错对象了小南瓜啊
- 我真的不是邪神走狗起点御井烹香
- 旺妻命梦廊雨
- 娱乐圈撩汉日常月亮和猫
- 和宿敌结婚当天一起重生了林知落
- 做你的靠山桃禾枝赵十余
- 都市最强赘婿南焱蹲鱼叶辰萧初然免费阅读
- 从元尊开始无敌于万界温柔是种毒
- 殇璃(倾城绝恋原作)雪灵之
- 陆夫人每天在线掉马甲江盛
- 网游之收集大师兰翔他哥
最新更新
- 带着系统发大财(美食成神系统)隐空人
- 奇门术师雪冷凝霜
- 重生之自重冰魄娃娃
- 我靠摆摊养夫郎三五余七
- 豪门婚色之前夫太野蛮四四暮云遮
- 司空牛角弓
- 苍壁书慕时涵
- 王爷,能不能不撩我!水墨染
- 还童陈灯
- 怪物实验室抹茶面巾卷
- 斗罗之让本体宗提前伟大肉沫砂锅粉
- 岁月间静水边
- 药仙静舟小妖
- 闪婚之抢来的萌妻律儿
- 穿书后成了皇帝的情敌林不欢
新书入库
- 怪物实验室抹茶面巾卷
- 九龙战婿陈玄嬉皮笑脸
- 九龙战婿陈玄苏云溪嬉皮笑脸
- 至尊狂婿陈玄嬉皮笑脸
- 文物不好惹木苏里
- 小甜O穿进了权谋文林不欢
- 奇门术师雪冷凝霜
- 学兽医的我在草原做雪豹干饭喵
- 傲娇仙君不要跑萌豆豆
- 西游之我在天庭996梦笔生花